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胡玉藜 記者 姜妍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2024年,脫口秀影響力愈發顯著,已然成為人們表達情感、宣泄壓力、探討社會議題的重要媒介。那些熟悉的脫口秀演員再次進入觀眾視野,他們用幽默消解刻板,將調侃解構荒誕,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回應著當下的關切。
不僅限于電視節目的舞臺,脫口秀的觸角早已深入社交平臺與短視頻領域。在這些更為碎片化的媒介中,段子成為新的傳播載體,與文學、音樂、影視的跨界結合,也賦予了這一形式更新的表達維度。這一曾在小眾地下文化中生長的藝術,如今躋身主流,成為解讀當代生活的文化符號。它承繼幽默的傳統,也以自身的方式回應著當下社會的集體焦慮。
“幽默”一詞最早由林語堂翻譯自英文“humor”,他通過創辦《論語》半月刊,試圖喚醒中國人對幽默作為生活一部分的意識。正如楊笠所言:“語言是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重要的權力。” 如今我們希望在脫口秀的舞臺上,尋找到這種新語言形式的力量。
鑒于此,界面文化策劃了系列報道——進擊的脫口秀演員,今天推出的是該系列的第七篇:《王越:這個家沒有人需要再次逃跑了》。

“大家好,我是王越,是個女演員。”
每次演出正式開場前,王越總是會和觀眾們互動幾句。這是王越個人專場《請回答1米58》的慣用開場白,作為一名四川籍脫口秀演員,近兩年她在川渝的人氣迅速高漲。
來看本場演出的觀眾中有一個顯眼的三口之家——二十四歲的女兒帶著父母一起來演出。“等會兒尺度可能有點大,我們父母能接受嗎?”王越拖著話筒向觀眾席后排的位置問道,坐在前排的觀眾們也跟著聲音的方向往后扭頭。“沒問題”,女兒用爽朗的笑聲表示回答,接著全場掌聲響起,尖叫聲和歡呼聲混在一起,拉開演出的帷幕。
將王越描述成是個“假小子”可能是一個挺過時的說法,但在某種程度上又符合大眾對其刻板的想象。她有即使戴著口罩走在街上也會被粉絲一眼識別出的身形,常年搭配寬松的衛衣、七分褲,還有被發膠噴過以后根根挺立的寸頭,綽號“王哥”由此而來。另一個愛稱“大甜甜”,則是源自王越剛進入社會不久,曾偶然被詐騙組織騙進“網戀小組”的經歷。

隨著這場演出的漸進,其涉及的現實問題也越來越深入:“王哥”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性別歧視;低學歷的“大甜甜”在就業市場面對的各種險象環生;以及,在還沒有變成“王哥”和“大甜甜”時的小王越,所經歷的原生家庭之痛。
表演結束已是晚上十點,王越要繼續返場,與觀眾們簽名合照。當下這刻,站在舞臺上的王越,眼神中略帶倦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她那依舊直立的頭發。有幾個年輕女孩陸續走上前和她擁抱,有的話沒說幾句就開始落淚,每到這個時候,王越會像女孩們的朋友一樣拍拍她們的肩膀,為她們打氣。
王越第一次在綜藝節目上露面,是2024年的《喜劇之王單口季》,那時她就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界面文化在王越巡演間隙中,對她進行了專訪,這篇文章歷時將近一年,一年過去,如今的王越已經是本季大賽中的季軍。
接受采訪的當天晚上,她在成都某喜劇俱樂部有一場拼盤演出。那天很冷,我們約在咖啡館見面,王越似乎習慣于充當照顧者的角色,剛一落座就詢問起是否有吃飯,在得到肯定答案后,她不太相信地撇撇嘴,“都這么講。”之后迅速拿起桌上的菜單,點了茶和薯條。
對話很快展開,期間方言和普通話不斷交織著——敘述一件事時,王越通常會用普通話,平靜的、客觀的、偏正式的;談到感受時,情感或激烈或溢出時則自動切換回四川話。這是一個對自己的語言表達非常謹慎的人,一旦內容出現沉重的傾向,她就會用喜劇的形式化解掉。
“好笑”是脫口秀演員站在舞臺上的使命,提起“喜劇的內核是悲劇”這句陳詞濫調,王越有自己的想法,她稍加激動地反問道,“可是所有事情的內核是不是都是悲劇?”

那個多出來的人
四歲時,王越的父母離婚,母親選擇離開老家外出打工,父親很快組建了新的家庭。留在老家的小王越和奶奶一起生活,從她在節目上提到奶奶的段子來看,很多人會天然地認為王越來自一個非常幸福的、能提供她支持與關愛的原生家庭。這是她童年明亮的那一面,留有奶奶印記的那一面。
在王越的眼中,奶奶是一個樂觀、堅韌、妙點子多的典型四川女性,經歷中年喪夫后,一個人將三個孩子拉扯大,奶奶就是王越眼中的超人。
從七歲開始,王越頻繁出現在學校上課上到一半就暈倒的癥狀,吃了兩年本地醫生開的藥也不見任何改善。一次高燒后,奶奶把她帶去當時縣城最大的醫院治療,過程中昏迷八天。模模糊糊的意識里,王越只能聽見媽媽和奶奶間斷的哭聲,感受到與之相伴的身體的疼痛。醫生將她診斷為罕見的川崎病,奶奶覺得不行,堅持要送她去市區最大的兒童醫院再次診治。在兒童醫院,王越一邊被醫生下達病危通知,一邊聽床前的奶奶講張海迪的故事。三個月后,她奇跡般地痊愈。
“從此我是死過一次的人了”,王越想。

童年時的王越,是留過長發的,“奶奶給我編的,”提到頭發她關于奶奶的回憶再次被勾起。十一歲時,她的童年即將迎來版本的另一面,這一年,姑姑的小孩出生,奶奶去了浙江幫忙帶孩子。于是,父親提出把王越接去自己新組建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建議。似乎,一切也由不得王越自主選擇。
父親的新家在距離達州300多公里外的德陽,當地的方言口音上會與達州有輕微區別,王越為了盡快融入新家庭,努力調整起自己的口音。
敏感的王越很快就察覺到父親想將她拽入新家付出的努力,但新生活的逼仄也是她必須要面對和適應的。在新家里,王越只能住在樓層過道處,沒有私人空間,連換衣服都不方便。家里還時常有父親生意上的伙伴來來去去,她每次只能等到別人下樓時迅速換衣服,“在那種情況下,你沒有辦法去選擇你能住的地方,因為沒有資格。”
“為什么沒有資格?”
“因為他當時已經有了單獨的家庭,我能感覺到自己是這個家庭里面多出來的人”,王越用非常平靜的語氣說道。
就是在這個階段,留著長發的王越,決定將頭發剪短。這是一個倒推的過程,短發是一個表象,剪發是一種行為,小時候的王越只是憑著直覺想要把長發剪短,“利索,不給人添麻煩”,當時的她迫切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個獨立、干練的強人。“和奶奶一起的時候,她每天都會給我扎頭發”,但去父親家后,“沒有人在乎我”。對小女孩來說,打理長發是一件花時間的事情,也會給身邊的人留下在意穿著、喜好打扮的印象,王越不需要這些,她覺得自己是這個新家多出來的人,而多出來的人,就應該做到不給人增添麻煩。

母親在哪兒呢?節目上,王越講過自己身為留守兒童的故事,拿著僅有的五毛錢去公用電話亭給當時在外打工的母親打電話,母親在電話另一頭哭,一分鐘五毛錢,母親剛好哭完一分鐘。
十七歲的一天,王越接到母親從成都打來的電話,這次母親帶來的是令人振奮的消息——她決定讓女兒搬來和自己一起住。電話另的一頭,王越反復和母親確認消息的真假,在得到肯定答復后,她掛斷母親的電話又立即打給班主任,興奮地說自己要退學去成都生活。
但快樂來的太過迅速,根本無暇顧及現實的因素,到成都后王越才了解到,因為她的戶口還在老家,就沒辦法立即在成都上學。她清楚母親生活的不易,最終放棄繼續讀高中這條路,轉去讀了中專。
從中專畢業后,拿著專科的學歷,進入社會的海洋里,她再次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多出來的人”。
社會的海洋
畢業后,王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幼兒園當實習老師,為了裝大人,她決定把學生時期留的蘑菇頭剪成短到不能再短的寸頭,在王越當時的認知里,頭發的長短會影響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我敢剪這么短的頭發,就意味著我不怕任何事情。”但這個行為卻讓家長們難以接受,這份工作她只做了三個月,之后又陸續干了不下十份工作。
因為學歷低,進入社會又早,王越能找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基礎的崗位,春熙路上的服裝店店員,寫字樓里的電話銷售,她都干過。有段時間,她因為工作需要頻繁喝酒,每次喝醉后就拉著朋友講一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那些痛苦的、遺憾的細節在講述中變得更加具體,但“每講一次,它們就會從我身體里少一遍。”那是王越最貧窮和不得志的人生階段,有時候連一頓飯都吃不起,公交車都不敢坐。
往前回溯,這就是王越日后成為脫口秀演員的草蛇灰線——在向朋友不斷的“傾訴”中,她展露自己的痛苦,放置自己真實的情緒,找到“我”的位置。直到2022年,她真的站上舞臺,成為一名脫口秀演員。
王越第一次看線下脫口秀是在成都的某喜劇俱樂部,此前,她只在手機上刷過視頻,并不知道還能線下演出。她在保險公司上班的姑姑想拉她入伙,正好公司與該俱樂部有合作,員工能免費去看演出,她就去了。表演結束后,大家拉了微信群,工作人員時不時地會往群里發一些喜劇培訓的鏈接,王越報了名。時間來到2022年3月,在培訓班學習不到兩個月的王越,開始上臺表演。
從開放麥到正式演出,從演出到壓軸演員,再從壓軸演員到開雙拼,最后辦專場、上節目,每一步,王越都比同行要快一點。在參加2024年《喜劇之王單口季》的節目錄制初,她只是抱著一輪游的心態,最終走到第四輪的她,比賽期間創作了三篇全新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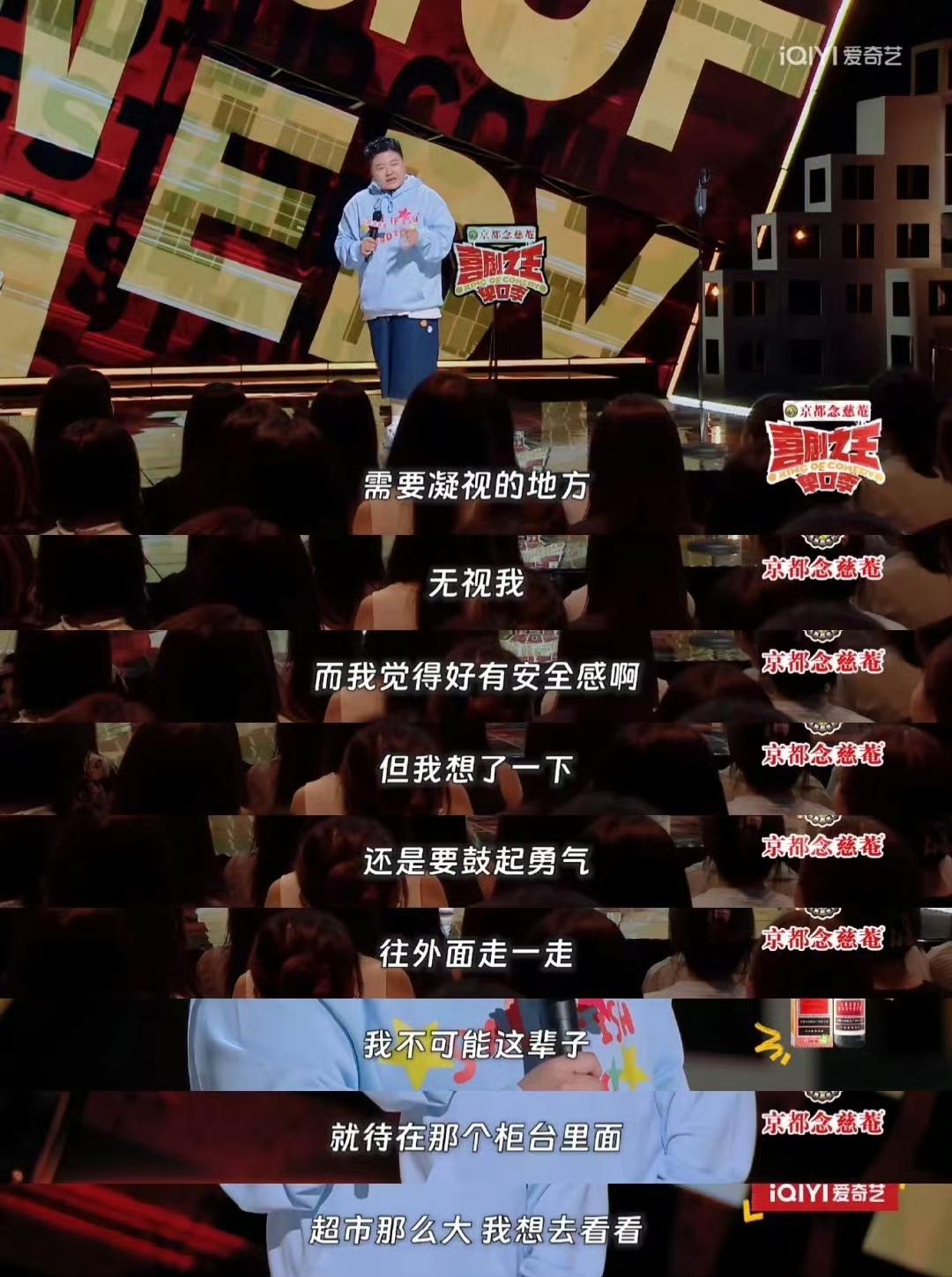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剛開始演出時她也受到過一些來自同行的指責,認為她的表演不能算是脫口秀。確實,在脫口秀演員里王越的準備方式有蠻大的差異化,她坦言自己幾乎不寫逐字稿,“我都是在腦子里過一遍”,要不然就是和嘻哈、潘老師一起吃飯的時候扯閑天,一頓火鍋下來,飯也吃飽了,段子也想好了。
嘻哈和潘老師是王越在成都的好朋友,同時也都是耕耘線下演出脫口秀演員,王越被同行批評時,第一個選擇傾訴的對象就是嘻哈。嘻哈在業內以脾氣直爽為名,是“俠女”,也是王越的偶像。她沒有什么安慰的套話,只是在電話里堅定地告訴王越,“不要在意”和“你會越來越好”。
參加完節目的王越確實越來越好,她的專場《請回答1米58》在新年之后成功出海——辦簽證、過海關、學英語,這些經歷逐漸滲進她的新段子里。她認識了更多的人,有了更多新的朋友,這些朋友在她眼中有趣,體面。但與此同時,她的微信簽名長期寫的是——多想想落魄的時候是怎么過來的。

“我很害怕自己忘記當初為什么想要站上舞臺講這些東西,害怕變得妄自菲薄,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這是一個非常女性的自審時刻,王越像是能預料到什么,因此她開始提前行動。
“所有人的愛”
2024年5月17日這一天,王越在成都舉辦了她人生中首場的專場演出。一個小前情是,前期演出在測試階段時,她講到原生家庭的部分流淚了,這讓她開始擔心正式演出時的效果。
但當王越站在舞臺上,眼見燈光緩緩亮起,照在她的臉上,也灑向觀眾席的瞬間,她終于松掉一口氣,“我看不見她們每個人的臉,但我能感受到底下坐的滿滿當當。”
她把從這場演出中收獲的反饋視作“所有人的愛”,形容觀眾是在用笑聲、掌聲、叫喊聲,真正意義上托著、拽著、拉著她跨過家庭這一關。
時隔半年后,再次在專場里提及父親、母親,王越已經能夠用身為單口喜劇演員的專業技巧輕松化解那些淚點,只是從很多細微的設計中,還是能看出她的“心軟”。比如演出里提到讀初中以后變得叛逆,事實上,王越就沒有怎么經歷過叛逆的青春期,之所以要做這樣的處理,是為了塑造自己的個性與父親的暴力進行一個對沖,“像是天秤的兩端”,讓大家更能接受一點。
王越的專場有一個固定的安可環節,每次演出結束后,她會返場隨機和觀眾聊聊天。巡演的前期,她收到過不少觀眾反應內容過于沉重的私信,于是她開始有意識地在安可環節中詢問觀眾,“會不會覺得今天的內容太過沉重?”
類似的小調整,是她與觀眾建立和維護關系的一種方式。有段時間,王越的生活里發生了一些讓她煩心的事情,當時的她對很多人和事都感到失望,“好像唯一不會讓我失望的,就是觀眾,”也是觀眾的鼓勵給足她底氣,讓她終于在今年的節目上徹底打開自己。
她擁有了直面痛苦的勇氣,她開始在舞臺上直面講述。
“這個家沒有人需要再跑了”
去年年底界面文化采訪王越的時候,她還沒有完全確定今年上節目時將要講的素材,但那時候已經有了創作的火苗,專場里也反復實驗過。她想要把母親的故事搬到舞臺上,讓更多人聽見。
于是母親的形象出現在《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是一個進出聯合國也能暢通無阻的四川女人,是一個被車撞過三次也還活蹦亂跳的樂觀女性,還是那個出走的母親。
十七歲那年,王越好不容易從德陽“父親的家”逃往成都“母親的家”,但“母親的家”,不是母親的家,其實是母親現任丈夫的家,王越繼父的家。她對母親感到愧疚,盡管男方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她總覺得母親是為了盡快接走她,才選擇和一個與自己不太有共同話題的男人結婚。
專場演出中有一個笑點——母親在王越很小的時候出走,本意是想帶她一起走,但最后因為她實在太胖,只能丟下她獨自離開。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她插科打諢了一下,像是要轉移話題的意思,“哦,那個啊,其實就是她當時沒有帶走我的能力,我心里面本來就有答案”。
“那你后來還有問過她嗎?”
“沒有”,王越怕,怕提問再次傷害母親。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的追問停在了這里。今年,王越在節目上用喜劇的形式給出她的答案:要跑,應該跑,還要早點跑,才會沒有人需要再次逃跑。
采訪接近尾聲,外面的天早已黑下來,王越起身準備去參加當晚的拼盤演出,“今天會有新的段子”,說到這里,她的眼睛亮了起來。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脫口秀演員是誰,為什么?
王越:嘻哈和潘老師并列。他們在舞臺上表現出的張力太吸引人了,真的在發光發熱。
界面文化:怎么看待脫口秀行業在國內的繁榮?
王越:我也沒覺得多么繁榮(笑),但肯定是好事情,因為每個人都需要放松。脫口秀這個行業可能沒法讓人忘記煩惱,但至少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可以讓人暫時剝離開自己的生活,有一點窗口。
界面文化:不斷尋找新梗、持續創新會是內容創作中最難的事嗎?
王越:難,這個對我來說有點難,因為我不是一個特別會寫梗的人。我不是那種坐在電腦寫稿的創作者,脫口秀對我來說也不是寫稿,是要脫口而出。我會和朋友聊,然后把梗聊出來。
最早參加的培訓課會教一些技巧,讓你的文字看起來不至于貧瘠無聊,國內的單口喜劇培訓體系都是有其繼承的嘛,也有一些翻譯的書,但我看不了,我是那種從眼睛進入到腦子的過程非常緩慢的人。
界面文化:脫口秀是只要好笑就夠了嗎?還是需要融入一些其他價值?
王越:對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我需要回答的,是觀眾需要回答的,就觀眾的層面需要什么。但如果我來回答,我會說好笑一定是首要的,又好笑又有表達的價值當然就能脫穎而出,但如果你就是純好笑沒有價值,你覺得夠了,那也可以。我覺得不用去評判,好笑何嘗不是一種價值。
我覺得就是雙向的,就是觀眾笑了,他給你反饋,你作為演員在臺上,那才是你價值的體現,如果脫口秀不好笑的話,那跟演講有什么區別呢?
界面文化:“標簽”和“金句”會困住你嗎?
王越:“王哥”和“大甜甜”不會困住我。我覺得標簽是讓觀眾最快認識你,金句就是讓觀眾最快記住你。不會把我困住,主要是我也沒什么金句。
界面文化:你如何預判脫口秀行業的未來?
王越:這個我沒辦法預判,但我確實是很期待能看到越來越多不同行業、不同身份、不同社會地位的人能走到脫口秀的舞臺上來,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真的會有一個主角夢、一個明星夢。我覺得脫口秀應該歡迎更多的人去上開放麥的舞臺,就像之前李誕說的“人人都會講5分鐘脫口秀”,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可能是大家離舞臺夢最近的一個途徑。
(本文按語部分寫作:徐魯青,文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