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中國人,包括我在內,多多少少對于日本政治家,我們都期待著他們什么時候道歉,好像日本這個國家你做什么都不重要,你得給我道歉這個事很重要。”在周末舉行的《妥協與對抗》新書分享會上,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王升遠這樣回應讀者讓他評價近期日本政壇變動的請求。
在高市早苗被稱有望沖擊日本首相的這些天以來,人們發現她在政見上的保守傾向,尤其是她多年來選擇在8月15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一事,讓中國民眾感到警覺和擔憂。
王升遠援引了日本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的發現,來解釋戰后日本有關戰爭記憶集體“錯亂”的原因:雖然中國在“十四年抗戰”上達成一致已有多年,但日本往往把1941年珍珠港事件當作戰爭伊始,在此之前侵略中國的行徑通常是被冠上“事變”的幌子進行的,日中戰爭在日本國民的意識當中一直是被隱瞞著的戰爭。“1945年的戰敗,在日本人看來是太平洋戰爭的戰敗,戰敗的終結只和美國有關,日美之間已經了斷,而日中之間的了斷一直都被擱置了。”

和平年代,思省民族曾經犯下的苦難尚且如此艱難,而在“極端”也即時勢比人強的時代,知識人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是妥協,是反抗,是沉默,抑或轉向?與王升遠展開談話的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在他眼中,這并不是個日本的地方性問題,中國知識人在現代轉型歷史迷局中,也同樣有內在的困境。
01 警惕“正義”之名的加害性

許紀霖指出,自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生成了一套“正當”的侵華理由:相比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的近代化,中國是野蠻的、原始的,日本感到有義務去幫助中國發展,填補這個文明的洼地。
“這是‘文明優先論’的辯護思路。”在他看來,許多非正義的戰爭都以“文明”的正義之名發動,但文明不是最高的價值,比文明更高的價值是人道主義、人權意識,是暴力的減少、保護和尊重個體生命。“不要以為高大上的東西就是深刻的,越完美越純粹越脫離具體的善背后往往蘊含著某一種惡。”
他觀察到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由于對戰爭沒有體感,總是容易說出一些輕巧的話,比如“不惜一切代價如何如何”,“我懷疑當他們說不惜一切代價的時候,是否他們覺得自己是不在代價之內的。”許紀霖提醒人們注意,在當下的東亞,戰爭陰云不僅沒有消散,還在多地凝結著,而從遠方戰場傳來的消息也告訴人們,戰爭的痛苦與恐怖是實實在在的,跟夠不夠堅強、有沒有勇氣無關。

鶴見俊輔是王升遠書中提到的一位日本戰后思想家,他也相當警惕以“正義”之名的加害性,尤其是正義與權力集于一身時的后果。鶴見曾在1942年加入日本海軍來到東南亞戰場,從軍經歷令他意識到,戰火中沒有道德完美主義存續的空間,墮落、邪惡也不再是單純的哲思客體,而是時時迫近、無法逃避、可知可感的日常。
當被堅信戰爭信念的軍隊士兵唾棄排斥,甚至私刑傷害時,他感知到這些充滿上進心的“純粹”之人或“正義”之士對于沒有滿足其標準的人來說,意味著何等暴力。善與惡、加害與受害、正義與非正義這類二分法,在鶴見眼中從此不過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
王升遠也用電影《朗讀者》進一步展開了他理解中的“制服”論:漢娜在納粹時期擔任集中營的管理員,她恪盡職守保證大門緊閉、防止囚犯逃跑,在一場大火中亦是如此,結果造成了大量傷亡,這讓漢娜在戰后得到了審判。法庭問她看著人們喪生火海于心何忍,她覺得她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發現她有個特點,她穿上的管理員的衣服,會給她帶來一種安定感。她的使命、道德,倫理全是由制服決定的。”
王升遠推此即彼,認為在戰爭中,“愛國”這個詞語有時也表現為一套“制服”,一種作惡的工具,讓許多人遭遇了如鶴見俊輔相同的情況。當時日本知識人一旦對于侵略行動表達出看法,就會被批評是“非國民”。這成了很大的帽子、標簽,成了所有“異端”力量發聲的緊箍咒。

02 弱者的抵抗之姿,于人的寬恕之道
在談話中,兩人皆提到德國戰后反思的歷史,其中就包括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發表的《罪責論》,雅斯貝斯把罪責問題區分成四類:法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罪責。
在他看來,戰爭責任追究中最棘手的是后兩者。前者要求人們“不拿‘我必須服從命令’當借口,罪行就是罪行,哪怕是奉命行事,都應該多多少少接受道德的評判”,至于后者,王升遠形容其是“非我的未然狀況之自覺與敬畏”。“即便感到無能為力,依然無法免除我們靈魂上的罪責感,而非責不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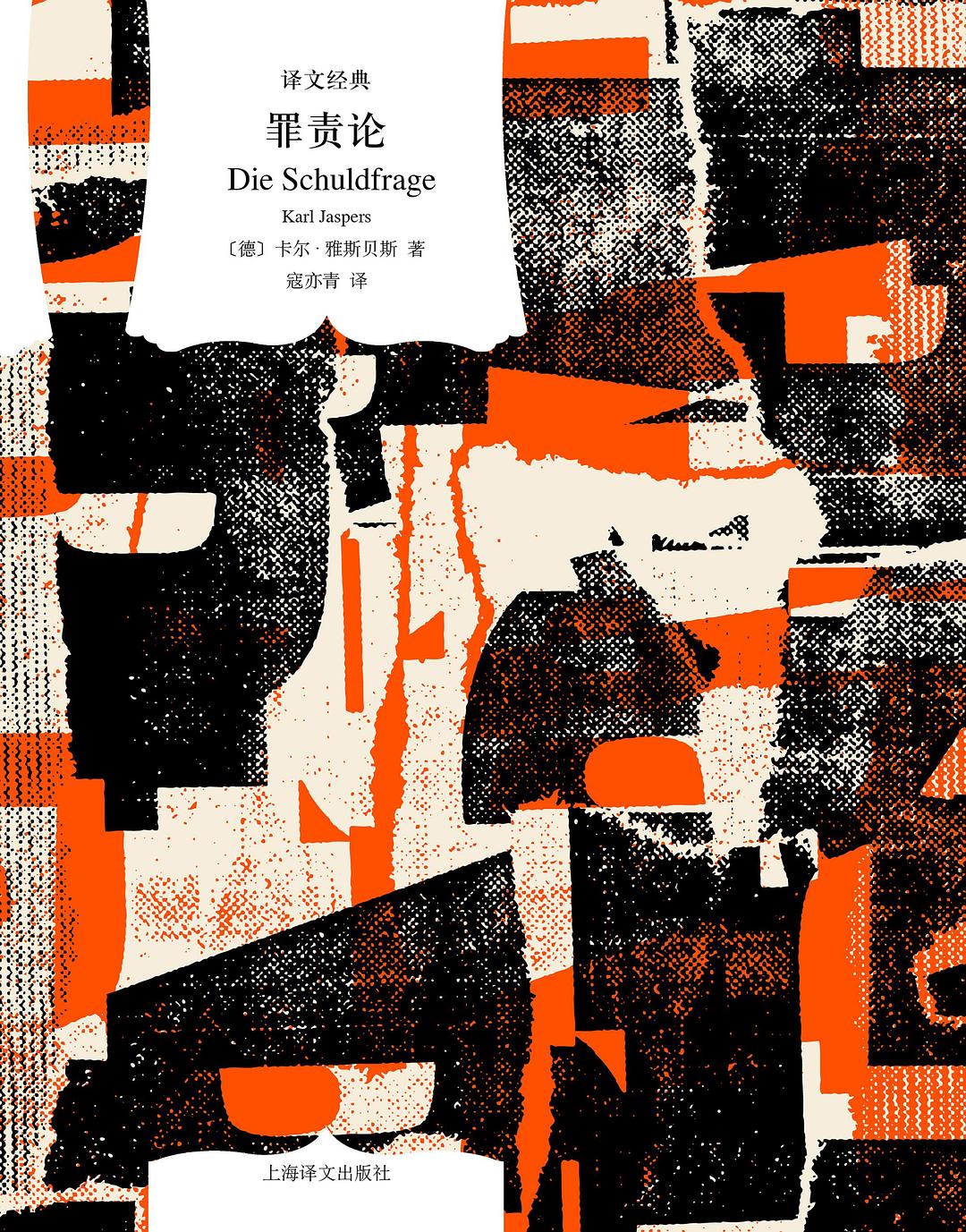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3-10
許紀霖同意這種反省的深刻性與要求之高,但他強調“道德、勇敢這類要求從來是一個自我實踐的結果,而非用來綁架別人。”楊絳去世時,知識界曾圍繞她和錢鍾書激起過一場爭論,他們超脫行走于世的姿態,被一些人質疑是放棄了家國情懷與天下責任的犬儒。許紀霖舊事重談是想表明,“理解沉默,這有個具體的情境。若是在極端的時刻,一個人的沉默很重要,不能有所為,但是能做到有所不為,這也是很了不起的。”
王升遠把這種沉默稱作“弱者的抵抗”:“剛猛的抵抗、進取者動輒出師未捷而中道崩殂,留‘人’清譽卻于“事”無補;而淡化個人譽望,保持一種能動、堅韌而堅定的應對方稱現實的‘理想主義’。”在戰爭爆發、政治語境收緊的極其惡的時代,不去做惡的基數,不為惡叫好喝彩也是基本的善。
當涉及歷史問題時,王升遠注意到東亞各國的外交詞匯中經常出現“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八個字,然而“歷史為鑒”也有產生變形后果的風險,使“面向未來”的關系遲遲不易建立,例如近來,中日兩國民間的極端對立傾向屢見不鮮,人們仿佛處在一條日漸惡化的如德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所言的“暴力的鎖鏈”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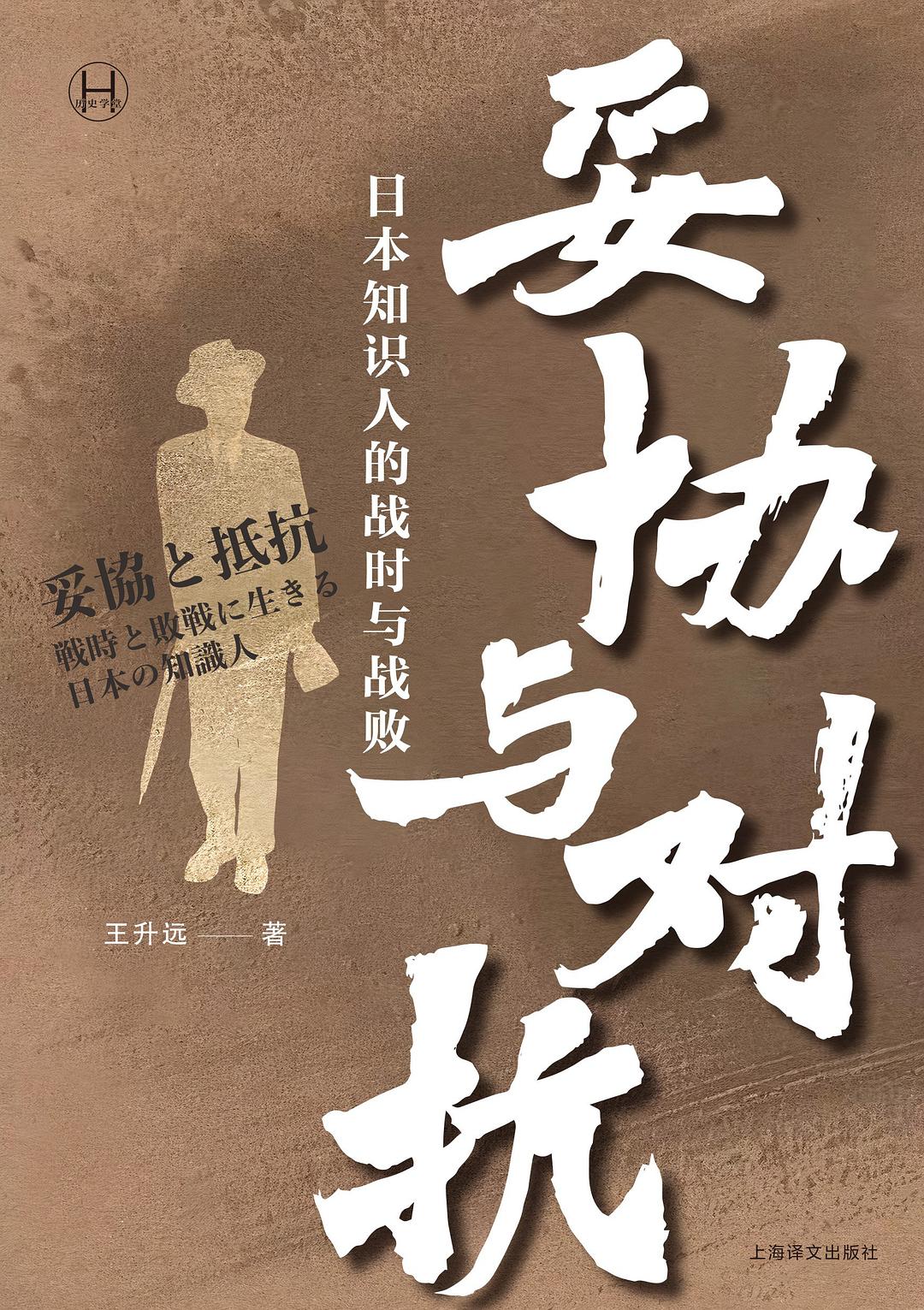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6
打破僵持境地的方法,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是懲罰與寬恕,日本思想家高橋哲哉后來基于此提出的是審判和寬恕。其中的寬恕并非指他人要求自己寬恕,而是嘗試寬恕一件自己始終沒法原諒的事情。“這不是道德義務,但這會意味著你如何面對自己,如何與自己相處,意味著打破暴力鎖鏈的一種可能性,”王升遠解釋說。



